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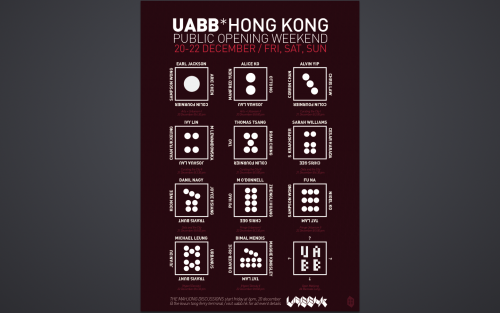

(原文刊登於12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)
「科學與藝術的活動,只有在不享受權利,只認識義務的時候,才有好的成績。以精神為勞作為他人服務的人,永遠要為完成這事業受苦。因為只有在痛苦與煩惱中才能產生高貴的精神。犧牲與痛苦是思想家與藝術家的命運,他們的目的是為那眾人的福祉。絕沒有心廣體胖、自得自滿的藝術家。」
──列夫托爾斯泰:《我們應當做什麼?》
政府為打造觀塘商業中心區,持續空降文化活動,十一月份抓走並起訴六名海濱天橋底的原使用者,權力、文化活動與都市仕紳化的曖昧關係,歷歷在目。上星期三(11日)非民選特首梁振英到訪,並為港深建築雙年展主持開幕禮,再度爆發衝突──場內五名參展的藝文工作者被趕被抬離場、部份參展藝術家被拒於門外、我與一眾觀塘使用者被過百名警察禁錮於示威區內不能離開,無緣目睹有份出席的巴塞隆拿市長在觀塘遇上抄襲巴市地標「受傷星宿」的歷史場面。幸好有行動者在繞道橋面擲下九米高的標語,寫上「國際街坊警告:慎防文創推土機」。可惜本地主流媒體未能咀嚼當中含意,只集中報導沒有人參與的「路姆西飛行大賽」。朋友怒罵,開幕禮為何不移師警署內舉行,而我在想,這個在一號場地的「反轉天橋底」計劃,名字改得真好。
被逐的參展者在網上發起聯署,要求以香港建築師學會為首的主辦單位公開道歉,卻換來令人絕望的回應──策展人認為場地供應者「起動九龍東」專重言論自由,容許作品帶有異議聲音(如黃宇軒帶有強烈控訴的作品,只寫上「想要的偏偏唔俾 唔想要的偏偏去起」十五個字),並說主辦單位只負責美術決定(artistic decision),是場外示威令活動失焦。可能主辦單位誤以為我是反觀塘仕紳化運動的頭目,竟然邀請本人參加第二階段開幕的「麻雀枱討論會」,還說可以一邊傾一邊麻雀耍樂,活動非常港深。文化評論人小西指出展覽用到法國馬克思理論家列斐伏爾的「城市權」(Right To The City)是可恥的事,而從展覽之初有四名藝術家退出,開幕有五名被趕走,到現在的麻雀活動,我卻仍然選擇相信如此滑稽的局面是源於策展人的無知,而不是全心羞辱挑釁。我拒絕出席,並要求策展人取消整個展覽──談美學之先,我們必須先談人權。得到的回應,是他們已花了一整年的功夫籌辦項目,取消展覽是無禮的請求。我反問,面對九龍東仕紳化,市民數十年的情感失落該如何梳理?
這就進入最難解答的問題核心了:文化藝術工作者在當下的發展之中應如何自處?我們的所謂藝術行動是否能給與傾斜的發展作出正面影響?
這個已經不是單單出現在九龍東的問題,而是政府與財團的發展手段已經必然牽涉到文化權利的買賣。「起動九龍東」拿著二千萬、一個公園、三個場地與一眾藝術家談判;市區重建局有一百億營運資金,無限特權,要是優秀的藝術家拒絕合作,馬上就向次一級的招手(如觀塘重建區貼上「完成」的倒胃海報);西九文化區更是夾著對文藝的熱誠與尊重,現在說要人,便有人。「家是香港」作為維穩項目,我們都能拒絕,但當它滲入舊警察已婚宿舍的 Detour,情況就變得複雜化。油街曾經自主出現的藝術區,被執達吏清走後空置逾十年,兩年前長實投得土地,現在為配合豪宅項目,需要「用」藝術了,藝術推廣處又再次把藝術家請回來。這些技倆,骨子裡都是同樣的文化亂倫。
數月前在「反轉天橋底」看見有外國到訪的藝術家出席活動,表演太陽能煎蛋,大受歡迎。我看著就覺得奇怪,從前這個橋底是全港最大型的廢紙回收中心,區內很多靠賣紙皮為生的婆婆把貨推到這裡就能賣。如今都市仕紳化,廢紙、垃圾、吊臂、躉船都不在當權者的美學範圍,必須趕走。然後看見回收中心被綠色膠布封起,再請鬼佬來煎蛋,大玩「環保」、「再生」、「綠色生活」、「公民參與」、「藝術介入」等等的語囈。參加同類型活動的人大多數不是來自本區,卻又從不缺人,因為這些普世的關鍵字太吸引了。
作為文藝最專業的一羣人,我們必須在當下反問自己,面對「文創推土機」的招攬應否拒絕,能如何拒絕,能拒絕多少,拒絕後可以怎樣。這樣不是為了在朋友身邊找出敵人,而是文化界應有的基本操守,現在高牆已經能把蛋殼視為藝術品去展現,我們的專業知識,的確能夠換成某種「城市特權」。現在的文化事業,問題已經不是缺錢,反而是有太多錢在流動,被規劃的文化空間,儼如被劃定的示威區,恐怕易入難出。